|
我,七瀨景,私立名苑女子學園三年級生,正在一條僻靜卻寬廣的道路上表示我心中極大的驚訝。 「咦?紅之森有傢伙跟妳告白了?」 「嗯。」 我身邊的初歌微微點著頭,還有一聲幾乎快聽不見的答應。 「這樣啊……」我把手提到腦袋後,書包在後頭晃啊晃的,我若無其事地吹了聲口哨。 「景?」 我半晌沒吱聲,初歌轉頭一問。 她那頭垂到腰際的黑長髮雖然還平整,不過她有些緊張的動作讓幾根髮絲被風吹了開來。 哎,別怪我常用「微微」、「有些」、「快聽不見」這類很不顯眼的副詞來形容初歌的動作,換做別人還瞧不出來初歌臉上有表情呢。 那我又怎麼看得出來?還跟學園裡出名的大小姐一之瀨初歌熟到她願意告訴我有個不懷好意的王八蛋對她告白呢?
──廢話,因為我跟她是戀人。
一之瀨初歌,私立名苑女子學園三年級生,卻跟我這個只會打羽球的人不同,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會長。說她是名門大小姐還算籠統,這世界上有多少個名門大小姐?在這種經濟起飛、到處都是商機的現代社會,在街上隨便撞一個,都可能是新興企業主的小姐少爺吧? 初歌跟那些小姐少爺不同。一之瀨家現傳的祖譜可以追溯到幕府時代的權臣,一路排下來的歷代祖先們,初歌說都是當代赫赫有名的人。戰後日本百業凋敝,當時的一之瀨家主把握良機賺了大把鈔票,還乘勢站上政壇,說有多風光就有多風光。 不過現在一之瀨家主,也就是初歌的父親──一之瀨朝堂,他的頭銜是一之瀨跨國集團理事長。一之瀨家做何種生意我不太清楚,總之跟微軟、殼牌石油、中國海爾家電集團平起平坐就是。 初歌就是這種豪門世家的大小姐。 她也確實符合大小姐的身分,鋼琴、花藝、茶道、品德、成績、外貌,該優秀的都很優秀,沒聽說過那次考試拿到第二名或比賽比輸的。 反正跟只會打羽球的七瀨景是不同世界的人。 「景?妳在生氣?」 「啊?」都怪初歌太漂亮又太有氣質,我承認我滿常看呆,這時我才想起那個不知被我丟到哪裡去的紅之森傢伙。 紅之森是我們對附近一所有名男校的暱稱,栽滿楓樹的林道是那所男校最大的特徵。 「我沒有生氣。妳當然會拒絕他嘛,我擔心什麼。」哼,紅之森盡是些被初歌外表所迷,靠性衝動欣賞女人的粗俗男人。「男人是靠下半身活著的動物」,不知道是哪個名人聖哲的話,說得真好。 初歌的美麗,絕對不只外在,然而能親近她心靈的人,寥寥可數。 聽見我的話,初歌安心笑了。 「……我還以為妳會生氣。」 「我為何要生氣?初歌很聰明,知道能彼此契合的人太少,絕對不會輕易放棄。我有自信,妳不會放棄我。」 初歌像匹緞子的黑髮被迎面的風吹向肩後,我因看見她難得的美麗笑容而高興。 偏僻而寬廣的道路走了好久才到中段,我們在一扇巨大的黑色鐵欄杆門停步,門旁有片木牌寫著「一之瀨」。 「景,我進去囉,明天見。」初歌彎腰朝我道別,我揮了揮手目送她消失在那條林道的樹影間才回家。 ──有時難免心裡不平衡,東京還有人的家裡可以栽種望不盡的林道? 一棟蓋在社區羽球館旁的二樓房子,除了在報社工作的老爸、當家庭主婦的老媽,還有個剛上高中一年級的弟弟,這就是極其普通的我家。 初歌有個弟弟,也跟她一樣優秀,是紅之森學生會的重要幹部,跟我成天只曉得玩網路遊戲的頑劣老弟完全不同。
※ ※ ※ ※ ※
初歌拒絕紅之森那傢伙的告白沒幾天,我跟她快樂的地下戀人生活就結束了。 名苑的規矩嚴格,校規是「嚴謹、純潔、有禮」,而女孩子與女孩子之間的戀情仍被普遍認為是件「骯髒事」。 我在走廊上與同學笑談前一陣子我領著羽球校隊拿下關東冠軍的驚險戰況,剛說到我漏接的一個吊小球,全校廣播就讓我心跳漏了一拍。 從廣播器傳出來的是新聞部廣播人員熱切激昂的聲音,內容同樣叫全校轟動。 ──我與初歌的戀情就這樣被赤裸裸公開了。 廣播的聲音震耳欲聾,我在其他聲音忽然消失的詭異寂靜中僵硬著身體,承受從天而降的龐大重量。 為什麼新聞部會知道?而新聞部又為何用這種方式拆穿?初歌呢?她怎麼樣了? 當廣播消失,同學們指指點點的竊竊私語鮮明起來,我看見人群自動讓開。 初歌孤零零站在那裡,咬著唇、蹙著眉,在同學刀割般的視線中顫抖。我看見她眼裡浮著一層水光,兩人的視線對焦後,水光潰決,初歌帶著奪眶而出的淚撲向我懷裡。 我像接住被強硬戳破外殼的雛鳥一樣張手接住她,初歌在我懷裡哭泣,按在她肩上的我的手不住發抖著,隨著她不住發抖的纖細肩膀。 我傻住了。 從來沒見過如此無助、如此不顧一切的她。將校規身體力行的初歌是老師與學生眼裡的模範生,優雅、矜持、有禮,然而她從四班一路奔來我所在的一班,在圍觀同學面前哭倒在地。 ──笨蛋。 初歌會不顧一切跑來,那正代表她無法面對那些責怪的眼神!我罵了自己一聲,這當頭還杵著不動,放著她被同學的目光凌遲? 我才拉起她的手轉身,就看見教歷史的明神老師站在人群中對我招手。
初歌低著頭,讓垂下的黑髮擋開任何侵略性的視線,僅只伸出虛弱的手讓我抓著直走。 途中我幾次擔心回頭,初歌始終維持這個姿勢不聲不響。我朝後頭跟來看熱鬧的同學狠狠瞪了幾眼,帶著初歌與明神老師一起進入心理輔導室。 心理輔導室為了讓被輔導人放鬆心情,鋪滿淺色溫暖的木板,沒有椅子,只有散在木板上的可愛方形抱枕。 我讓初歌靠在牆邊,不經意看見她那雙總是閃耀光采的眼失去亮度。我想了想,背對著跪坐她身前,獨自面對老師的質詢。 「七瀨,茶。」端來兩杯熱茶的明神老師慧黠地笑了笑,把熱茶推給我。「表情別這麼兇,我可不是來審問妳們兩個的。」 ──好好待在這,我去應付外頭好奇的同學們。 老師留下這句話就出去了,輔導室內略顯窒悶卻安靜無比,我盤腿坐在初歌身前,等她有所動靜。 當熱茶的蒸氣消失,開始轉涼時,初歌才慢慢抬起眼睛。左右張望一眼,確認過這裡只有我跟她,初歌忽地扯開一個虛弱的微笑,然後抱緊我放聲大哭。 初歌撲上來的衝力並不大,哭聲卻差點撞倒我。 我靜靜聽著她哭,在心裡後悔不已:我早該想想事情拆穿後,初歌該怎麼辦。我是個普通人,普通到即使是個拉子,影響層面也只限於我家,初歌卻不同。 她是個承受各方期望而長成的孩子。希望她聰明機敏、希望她品德良好、希望她美麗出眾、希望她不辱一之瀨這個姓,眾多家族親戚,以及聯姻可能對象的無數個希望塑造了優秀的一之瀨初歌大小姐。 她與我首次見面,是為了與紅之森的聯誼羽球賽,而被選為雙打選手的初歌羽球打得很爛。這也難怪,沒有哪個理事長會希望自己的千金女兒打得一手東南亞才盛行的好羽球。 基於不知何時根深蒂固的「參加比賽就要有好成績」觀念,即使紅之森已經表明,聯誼的雙打賽不過是男選手掌控全局,女選手只要一動不動站著就能結束一切的白痴表演,初歌還是一臉認真找羽球校隊長的我討教。 符合週遭人的期望,我想這就是她的人生觀吧。 沒有人會期望她與一個女孩子談戀愛,不期望也就罷了,橫列在她面前的是凶猛的責備與厭惡。 小時的初歌喜歡爬上樹眺望遠方,聽說曾被長輩狠狠教訓一頓,噩夢般的遭遇讓乖巧又聽話的她從此失去一項興趣。「……其實我很怕挨罵。」初歌曾說過這樣的話,她的世界教她如何贏得讚美、避免缺陷,同時也避免挨罵。完成大大小小別人的期盼,一之瀨大小姐這樣活了十幾年。 教會她什麼是自己的是我,在一次又一次的羽球指導裡。 什麼是她想要,不是別人逼著她獲得的,我們在午餐的樹下討論很久,我也看著認真的大小姐慢慢變成擁有自我的初歌。 最後,初歌選擇的自我包含了我,七瀨景。 不知道初歌有沒有想過這個後果,我只知道她還沒做好心理準備。面對周遭無聲的責罵,她無法放棄我,放棄就等同於摧毀這陣子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自我。矛盾掙扎的結果,就是現在這般,不知該怎麼辦地大哭,像個脆弱的孩子。 我肩膀的制服濕了一片,初歌還沒打算停止,我看見明神老師輕手輕腳推開門看著我和初歌。 一堂課過去了,初歌抱著我哭了整節,像是要發洩從小到現在所有被壓抑在期望底下的負面情緒。 後來,初歌轉為小聲啜泣,斷斷續續說了始作俑者是那個被她拒絕的紅之森的王八蛋。 ──媽的,聯誼賽看我怎麼痛宰你! 追究誰拆穿或者如何拆穿已經於事無補,我告訴初歌她和我將面對的情況,大概是一個人面對富士山的樣子吧。 「……富士山?」初歌眨了眨眼,有些疑惑,我這譬喻用得很怪。 「妳把它當作整個社會好了。」初歌默然,我揩去凝在她眼下的淚滴,把涼掉的茶端給她。 「……初歌,妳喜歡我嗎?」 初歌蒼白的臉頰一紅,輕輕點了頭。 「我是個女孩子唷,這樣妳還喜歡我嗎?」 「景,我喜歡妳,可是……」初歌皺起眉,不知怎麼回答。 「這麼說好了,妳認為喜歡我是件不對的事嗎?」 「當然不是!但……」初歌雖然立即否認,卻顯然無法跨過那道「期望」的高牆。 迎合期望是維持十幾年的習慣,三言兩語想打破是不可能的。我笑了笑,拉過她的手緊緊握著,希望能給她一些自信。 「知道不是錯事就好。初歌,待會回班上,妳要抬頭挺胸。記住,妳沒有做錯事,更沒理由畏懼些什麼。」 初歌低著頭沒有說話,我拿過那杯給我的茶一口灌下,順手搶過她手裡的半杯涼茶喝乾,拉著她起身。 「……我…我會努力。」初歌站起身來,給了我承諾。 「那麼……今天沒有練習,放學後我去妳家。」 初歌終於笑了,我摸摸頭,自己都有種「給獎品」的感覺。
我牽著初歌走出心理輔導室,往三樓教室走。 沿途經過不少教室,不論是裡頭的老師還是學生,都暫停上課,在透明的窗戶裡目送我們經過。 實在不願探究那些視線究竟混合了多少情緒,我只想轉頭大吼:「專心上妳們的課!」 我換了位置,讓初歌走在外側,戶外的風和陽光至少沒那些視線來得礙眼。 在一班教室轉角處,我拍拍她的腰,輕聲說道:「勇敢些,放學後我一樣在校門口等妳,什麼都不會改變。」 我揮了揮手見她往四班教室進去,才抬高頭進入我的教室。 ──好煩人的瑣碎交談聲。 就在我想拍桌大叫「有什麼想說的大聲講出來!」時,明神老師才踱了進來準備上課。 半節課很快過去了,老師似乎在趕進度,歷史軼事少講許多,原本我還料想能聽到些亞歷山大東征的趣事,比如這麼長的戰線要如何顧及補給,這真是我看電影最大的疑問。 老師在托勒密成為埃及法老的時候結束課程,接著發生的事情令人措手不及。 「七瀨。」 老師拿著點名簿,我舉起手。 「妳與一之瀨在一起時,知道總有一天會被發現嗎?」 全班頓時騷動是可以想見的,我差點從椅子上站起來。 「……我知道。」不曉得這句話是真在我嘴裡轉了轉就吞進去,還是明神老師故意,我看她似笑非笑地把手放在耳朵邊:「嗯?七瀨請說大聲點,老師沒聽見。」 「我知道!」想到哭花臉的初歌,我忽然生起氣,大聲回答她。 同學又是一陣煩人的嗡嗡議論聲,怎麼?我跟初歌在一起又不是犯罪,我不能理直氣壯說話? 「嗯,看來妳有心理準備了。」明神老師晃了晃手裡的筆,一臉若有所思。 「那麼……妳知道女孩子喜歡女孩子是……嗯……不太常見的嗎?」 很感謝老師的斟酌用詞,不過意思是一樣的,我聽見後頭有人不斷講著『什麼不太常見,是不正常吧。』、『就是嘛』、『沒想到會跟同性戀同班』、『好髒…』、『萬一她靠過來要怎麼辦啊?』。 我壓下嘴裡差點衝出來的「去妳的,我沒事幹嘛靠近妳!」,決定直接面對老師的問題。 「老師,我想請問妳一個問題,妳與妳先生談戀愛時,有考慮過性別嗎?」 明神老師眨了眨眼,沒有回答,但是我看見她的眼神鼓勵我繼續說下去。 「我的戀愛觀不存在『性別』這項因素。我喜歡初歌,不是因為她是女孩子,我喜歡她的認真,還有那份堅強外表下的脆弱。我對她心動,就像妳們看的言情小說裡那種主角間彼此動情的心動……」 後面傳來噁聲與噓聲,我置之不理。 「大家都清楚喜歡是種什麼感覺,難道我要因為對方是個女生或男生才去決定我應不應該喜歡她或他嗎?看外表、看背景、看性別才決定要喜歡上一個人,那不嫌太現實了嗎?妳喜歡的到底是那張臉、那些錢,還是那堆能讓妳懷孕的精蟲!」 全班鴉雀無聲,我微微喘著氣。 明神老師輕咳一聲打破寂靜:「……七瀨,妳家人知道妳與一之瀨的關係嗎?」 「老師,『關係』這兩個字很容易讓人妄加揣測,我跟初歌是單純喜歡彼此。」 我眉間皺起,老師知性的眼眨了眨:「抱歉,我用錯詞了。」 「……一大堆只會自己想像的人全把同性戀愛與性劃上等號,拜託腦袋別裝漿糊了,普通男女在一起能約會、看電影,同性在一起就得二十四小時SEX?」 我怒火未消,忍不住自言自語罵人,才不管後面那群有沒聽清楚,我又抬頭直視老師:「他們會支持我的決定。」 ──哎,我想他們會很震驚吧?然後問一句:「妳決定了?」然後看我點頭,無力阻止。 在這裡我要先向他們說聲抱歉,儘管他們仍有微乎其微的機會反對,此時我卻只能自以為是將他們抓來當捍衛的盾牌。 如果現在我有半點退縮遲疑,初歌僅有的一張鐵盾將會消失,在她能像我一樣坦然面對惡意之前,這些殺傷威力大的目光由我抵禦。 明神老師似乎在思考什麼,我又補充一句:「傳宗接代的事情,讓我弟去煩惱就好。」 老師有些愕然,這時教室外傳來放學鐘聲,為這堂疾風驚雷的歷史課畫下句點。 明神老師臨走前,感謝我讓她做了些Lesbian的觀察紀錄,我不置可否聳聳肩。 要說我是拉子也無不可,我喜歡的初歌是個女孩子沒錯,我不太在意別人怎麼替我貼標籤,只是我更喜歡「戀愛是無性別的」這句話。 今天放學時間的教室沉默得很詭異,然而我無心理會班上同學,只想快些到校門口等初歌,真不曉得這堂課她怎麼面對班上的同學和出名傳統保守的理化老師大石。 「……七瀨同學。」 才剛收好書包,背後忽然有人小聲叫了我。 我沒好氣轉過頭去,還以為誰要來找麻煩,卻原來是班上挺內向的杉崎。 「嗯……那個……」 杉崎扭扭捏捏的,不過她與我講話卻惹來不少同學注目。 「嗯…我……嗯……」 我看看錶,兩分鐘了耶,初歌已經在校門口等了吧。 「杉崎,妳有什麼話想跟我說嗎?」如果是平常,我大概會把手放到她肩膀上鼓勵她吧,不過這種時候還是別這麼做比較好,誰知道會被想成什麼不規矩的行為。 「那個……」又過了一會兒,她才終於鼓足勇氣,衝著我說一句:「七瀨同學,妳跟一之瀨同學要加油喔!」然後就跑走了。 啊…… 我抽了抽鼻子,拿著書包快步往校門口過去。 ──說實在,還挺感動的,富士山前不只我和初歌兩人。 |
雛鳥之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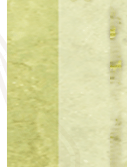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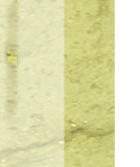
| 〉─《雜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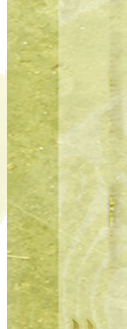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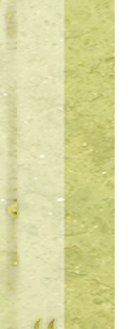

| 伯爵的天鵝湖 | 《 │ 》 |
